近日,內蒙古巴彥淖爾市烏拉特后旗烏蓋蘇木東烏蓋溝突發山洪,致使12名野外露營人員遇難——這一沉重事件再次將極端天氣下的防災體系推至公眾視野。當暴雨頻頻“光顧”北方、屢次突破防洪標準,我們是否忽略了系統性防御中最關鍵的一環?
針對這個話題,近日,《每日經濟新聞》記者(以下簡稱“NBD”)專訪了國際水文科學協會(IAHS)前副主席、城市水循環與海綿城市技術北京市重點實驗室主任、北京師范大學水科學研究院徐宗學教授。

“在山洪易發的汛期,切勿在行洪區域逗留。”徐宗學提醒道。
面對超標準暴雨洪水,徐宗學認為,根本出路在于“為水讓路”。他建議,結合城市更新與城中村改造等,建設下沉式公園、綠地與人工河湖,將其作為特大暴雨發生時的臨時滯洪區。同時,他也呼吁加強全民防洪避險教育,提升全社會對洪水災害的敬畏和防范能力。
問診:傳統少雨北方頻遭暴雨侵襲,防洪體系短板何在? NBD:近期北方多地突發特大暴雨,這些地區傳統上屬于少雨區,但出現了極端降水情況。從你的觀察來看,與過去相比,北方城市面臨的暴雨災害有哪些新特點? 徐宗學:從水文周期規律看,今年北方的暴雨雖然感覺異常,但其實符合水文周期性特征。以北京為例,從2000年前后到2012年“7·21”暴雨之前,基本處于枯水期,年降水量偏少。但2012年至今屬于豐水期,降水量明顯增多。這種周期性變化在氣象和水文上是正常的。
今年的特別之處在于,暴雨發生地點多且分散,缺乏明顯規律性。與1998年長江流域大范圍暴雨洪水不同,今年暴雨呈現明顯的區域性特征,比如北京密云、河北涿州與易縣等地的暴雨都屬于區域性暴雨。
從災害分布來看,今年較多受災嚴重的區域恰恰是當前防洪體系的短板所在,或者說沒有來得及充分治理的區域。這些地方既不在大江大河的重點防護范圍內,也不在海綿城市建設的覆蓋區域,中小河流治理可能又尚未完全覆蓋,可以說是當前防洪體系中的薄弱環節。
NBD:除了大家常說的排水系統跟不上,還有哪些容易被忽略的防洪風險點需要特別警惕? 徐宗學:在北方地區,很多河流可能近20—30年甚至40—50年都沒有發生過洪水,老百姓覺得這些地方是安全的,有時會在干涸的河床里堆放垃圾、建設農家樂,甚至有些地方在河漫灘上建房子、搞養殖、種植農作物。河漫灘的土地特別肥沃,因為是從上游沖刷下來的淤積物,富含養分,種莊稼長勢往往特別好。但如果發生洪水,老百姓常常措手不及。這種情況在南方會好很多,因為南方洪水多發,老百姓的防洪意識比較強。
歷程:從海綿城市到韌性城市,洪澇災害應對思路變遷 NBD:你提到我國防洪體系建設,能否介紹一下1998年長江特大洪水以來我國防洪工作的重點轉變? 徐宗學:我國防洪體系建設經歷了幾個重要的發展階段:1998年長江特大洪水發生后,國家投入數千億元重點治理長江、黃河、海河、珠江等大江大河。這項工作持續了十余年,使大江大河防洪能力顯著提升。
隨著大江大河治理取得成效,近10年來,重點轉向中小河流治理。現在國家每年都會給地方政府撥付專項資金,用于中小河流治理。這項工作采取的是分批治理的方式,逐步推進。
2012年的北京“7·21”特大暴雨是另一個重要轉折點,直接推動了城市防洪工作。隨后,國家提出了海綿城市建設。相關城市開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,使城市防洪排澇能力得到顯著提高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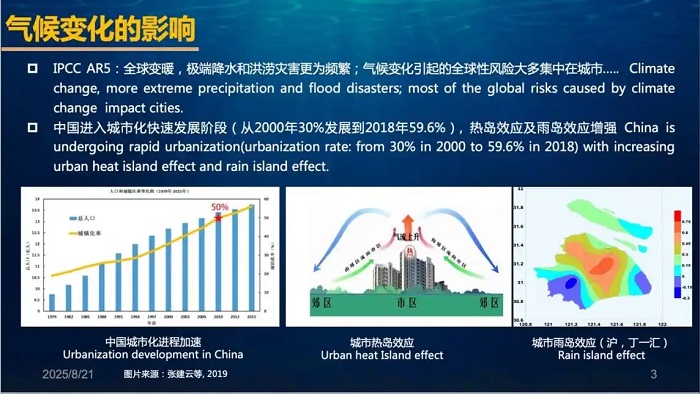
NBD:這些年,“海綿城市”“韌性城市”等概念先后提出,海綿城市在應對特大暴雨時是否有極限?公眾應該怎么理解這個“極限”? 徐宗學:對海綿城市功能需要有一個正確的認識。海綿城市已從早期的“小海綿”(以雨水花園、生物滯留池、透水鋪裝等源頭減排措施為主,可應對1—5年一遇降雨)發展為“大海綿”體系,整合了城市河湖、排水管網等系統,形成更為綜合的雨洪管理架構。
2021年,國務院提出城市內澇治理“16字方針”,將防御體系分為四個層級:源頭減排(如應對1—5年一遇降雨)、管網排放(如應對5—10年一遇降雨)、蓄排并舉(如應對10—50年一遇暴雨)、超標應急(遇超標準暴雨時啟動應急響應并轉移人員,首要保障生命安全)。
以(2021年)鄭州“7·20”特大暴雨為例,這種極端強降雨對城市排水系統構成嚴峻考驗,遠超海綿城市設計標準。在這種情況下,必須啟動應急響應機制,優先保障人員安全。
海綿城市不是萬能的,它主要解決的是常見降雨引發的內澇和雨水污染問題。近年提出的“韌性城市”更進一步,強調災后快速恢復城市生命線功能。
應對:建議結合城市更新工作,逐步恢復被侵占的水體空間 NBD:你提到南方和北方城市在地質等條件上存在差異,對于北方城市,在推進城市建設過程中,如何因地制宜? 徐宗學:南北方氣候和水文條件有著根本的不同,這種差異直接決定了技術路線的不同。
南方城市雨量充沛,可以大量采用雨水花園等綠色基礎設施,既美觀又實用。北方城市干旱少雨,可以多建設蓄水池、下沉式廣場等基礎設施,比如將體育場下沉2米設計,平時正常使用,暴雨時作為臨時蓄水池。
中國幅員遼闊,城市形態與地質條件呈現出豐富的多樣性。位于山前平原的城市往往面臨山洪的威脅;建于山坳之中的城市需要特別注意地質災害;沿海城市必須應對風暴潮等挑戰;丘陵地帶的城市需要解決地形高差帶來的排水問題;而沿大江大河兩岸建設的城市則要統籌考慮大江大河的行洪安全等。這種復雜多元的城市格局,決定了海綿城市建設必須堅持“一城一策”的基本原則。

NBD:隨著極端暴雨事件頻發,我們當前的排水標準是否需要進行重新評估? 徐宗學:這個問題很關鍵。
當前,我國城市防洪排澇存在三套標準體系:住建部門排水標準要求一般地區應對2—3年一遇降雨,重要地區3—5年一遇;內澇防治標準要求,通過泵站等設施實現20—50年一遇降雨不發生內澇;水利部門制定的城市河流防洪標準,則按50—200年一遇洪水設計河道行洪能力。這三套標準分屬不同部門,計算方法不統一,排水標準按降雨量、防洪標準按流量系列計算,缺乏有效協調。
通過歷史對比可以看到,當前許多城市的蓄水空間減小嚴重。在沿江沿湖等地區,許多湖泊、水塘、河溝在城市開發中被填平,天然的蓄水空間急劇減少。在多山的區域,天然的山洪溝被填平用來修建道路或建筑。但這些水塘、湖泊或溝渠是經過千百年來形成的天然行洪通道與蓄水空間,其存在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。這些改造,比如一條排洪溝被平整后建設為道路,可能使得原本明顯較小的洪澇風險,變成了隱蔽但更大的洪澇風險。
為了逐步緩解城市內澇問題,建議建立多部門協調機制,統一計算方法,實現排水、除澇及防洪標準的有效銜接。另外,結合城市更新工作與城中村改造工程,建議逐步恢復被侵占的水體空間,增強城市的調蓄能力,同時推行智慧化管理,加強管網維護與清淤。
治理:城市防洪系統建設,本質是“還歷史的欠賬” NBD:很多老城區暴雨積水問題嚴重,除了大規模改造管網,有沒有更經濟實用的“微創手術式”解決方案? 徐宗學:老城區積水問題根源在于歷史欠賬多——排水管網標準低、天然蓄水空間被侵占、行洪通道受阻。
治理路徑總結起來主要有三點:第一,適度提升城市的管網排水能力,確保雨水及時外排;第二,增強河道的行洪泄流能力,保障洪水安全下泄;第三,增加城市的蓄水空間,通過建設下沉式綠地、雨水花園、公園和廣場等,主動為洪水提供滯留場所。
當超標洪水來臨時,若沒有足夠的空間容納,雨水必將涌入街道和社區。因此,與其被動防御,不如主動通過空間規劃預留出滯洪區域,這才是提升城市韌性的治本之策。
如何增加蓄水空間?我認為,可以充分挖掘城市公園、綠地和停車場的暴雨蓄滯潛力,推行“平戰結合”的韌性空間理念。在特大暴雨應急情況下,應優先將公園湖泊、下沉綠地作為臨時蓄滯洪區,部分非住宅區的地下停車場也可在緊急清空后用于蓄水——以可承受的局部淹沒代價,避免造成更嚴重的城市內澇損失。通過“平時休閑、災時蓄洪”的雙重功能設計,使綠色基礎設施成為城市應對極端降雨的彈性緩沖區。北京溫榆河公園就是很好的范例。
多年前,我曾應歐盟邀請訪問過西班牙巴倫西亞市——一個80萬人口的海濱城市。它在城市中心地帶保留了一條天然排洪溝,溝底平坦,平日作為市民休閑空間,暴雨時成為高效行洪通道,大大提高了城市的防洪除澇能力。

排洪溝為圖上貫穿城市的綠色區域
NBD:每次暴雨,地鐵站和地下車庫進水總是讓人揪心。目前有哪些經濟可行的技術手段,可以防止雨水倒灌? 徐宗學:目前,多數地鐵站入口設有20—30厘米的擋板,這對一般平地積水是有效的。但低洼地段需特殊加強防護,比如廣州2021年某地鐵站進水,據了解就因該車站位于低洼地段,常規擋板高度不足。
對小區地下車庫,須常備沙袋、插板式防洪擋板等裝備,并保證排水泵系統狀態正常、配備應急電源。對于老舊車庫改造,重點是強化入口防倒灌能力,同時優化周邊排水路徑,避免雨水向車庫匯集。
對于上方為綠地、廣場等非住宅建筑的地下車庫,應提前規劃其在極端暴雨下的應急功能——緊急轉移車輛后,將其作為臨時蓄水池使用,主動容納部分洪水,也是減少城市洪澇災害損失的途徑之一。
要接受“超標洪水下損失難免”的現實,關鍵在于區分空間重要性——住宅和核心設施嚴防死守,非核心區域則設計為可淹空間,在保障人員安全的前提下,有效分擔城市洪澇風險。
公眾:加強防災避險意識,汛期絕不可在河道、河灘、溝道露營逗留 NBD:公眾能為城市防洪做些什么?比如社區自發清理排水口落葉,儲備沙袋等,這能起到多大作用?從水文專業角度,你對公眾還有哪些建議? 徐宗學:清理落葉、儲備沙袋、檢查排水泵站等,這些措施對于應對小型內澇問題是十分有效的。在特大暴雨來臨時,雖然地下管網可能無法及時排泄來水,導致小區進水,但這些基礎準備仍然能為居民爭取寶貴的緩沖時間。物業和居民共同做好這些日常工作,是防洪的第一道防線。
從水文與防災的專業視角看,提升公眾的防汛意識與避險常識,是減少人員傷亡最關鍵也最迫切的環節。
例如,近期內蒙古巴彥淖爾市烏拉特后旗山洪,致使12名野外露營人員遇難,這一悲劇再次警示我們,在山洪易發的汛期,絕不可在河道、河灘、溝道等行洪區域露營或逗留,這是防災避險的基本常識。提高公眾對自然災害的認知與敬畏,加強自我防護,是避免類似悲劇重演的根本所在。
過去的宣傳工作大多集中在“節水”,而“防洪避險”宣傳嚴重不足,尤其在北方干旱地區。社區工作者可以定期進行防汛宣傳,向居民普及遇到洪水時的避險常識,比如盡量避免外出,遠離積水區、行洪區,并警惕積水中的電線,讓公眾對洪水的破壞力有更全面的了解和敬畏之心。
NBD:結合你的觀察,對城市發展和公眾認知還有什么總體建議? 徐宗學:要認清海綿城市的局限性,海綿城市有用,但非一勞永逸。它主要解決中小降雨問題,遇到超標準特大暴雨,必須啟動“超標應急”預案,核心是保障生命安全。任何城市防洪設施都有其設計標準和承載力上限,無法應對極端情況。我們的認知和能力始終存在局限性。
公眾也需要樹立“與洪水共存、與風險同在”的理性認知。我們要接受“人水和諧”的理念,這意味著我們需要適當改變理念,同時結合城市更新工作和城中村改造工程,盡可能增加更多的蓄水空間,以增強城市的整體防洪能力。城市防洪的本質,是在有限的經濟技術條件下,通過工程與非工程措施結合,提升整體防洪韌性,學會與自然風險共存。
來源:每日經濟新聞



